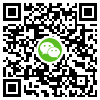人身生命保险被视为对家人的最后承诺,然而,当这份承诺遭遇理赔争议,亲情与法律的碰撞往往令人唏嘘。以下是一个发生在2024年夏天的真实故事,讲述了一份寿险保单如何将一家人推向法庭,追寻逝者的遗愿与公正。
一份为爱投下的保单
2024年6月,浙江宁波的刘先生,一位45岁的货车司机,突发心梗不幸离世,留下了妻子林芳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。两年前,刘先生为家庭投保了一份人身生命保险,保额100万元,受益人指定为林芳。他曾对妻子说:“我整天跑长途,路上风险大,这份保险是给你们娘仨的保障。”林芳珍藏着这份保单,将它视为丈夫对家庭的最后托付。
刘先生去世后,林芳怀着悲痛联系保险公司,提交了死亡证明、医院诊断和保单副本,希望尽快拿到赔偿,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。然而,保险公司审核后却拒绝赔付,理由是刘先生在投保时填写健康告知表时,未如实披露三年前的一次高血压诊断记录。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:“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,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拒赔。”
告知义务的争议
林芳百思不得其解。她回忆,刘先生投保时确实提到过偶尔头晕,但从未正式确诊高血压,体检报告也未明确记录。业务员当时说:“这点小毛病没事,填表不用写得太细。”如今,保险公司却以“隐瞒病史”为由拒赔。林芳翻出《保险法》,发现第十六条规定:“保险人对投保人的询问应明确具体,投保人需如实回答。”但健康告知表上只有一句笼统的“是否患有慢性疾病”,并未具体列明高血压。
不甘心的林芳找到了一位专攻保险纠纷的律师何静,决定起诉保险公司,要求履行赔偿义务。她对何律师说:“老刘走得突然,留下的债还没还清,两个孩子还在上学,这笔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”
法庭上的情感与法理交锋
2025年1月,这个案件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何律师在庭上直指关键:“《保险法》第十六条要求保险人对健康告知的询问应明确具体。本案中,健康告知表未明确列出高血压,业务员也未尽到询问和解释义务,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赔,显失公平。”她提交了刘先生的体检记录,证明其高血压症状未达确诊标准,且死亡原因与高血压无直接关联。
保险公司的律师则反驳:“投保人明知自己有高血压症状却未披露,违反如实告知义务。根据《保险法》司法解释,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。”他们出示了刘先生三年前一次就诊的门诊记录,显示医生曾建议他“关注血压”,以此证明他隐瞒了健康状况。
庭审中,林芳哽咽着说:“老刘为了我们娘仨,起早贪黑跑货运,买保险就是怕我们受苦。现在他走了,你们却说他撒谎,这对得起他的心吗?”她的陈述让旁听席上的亲友红了眼眶。
判决的平衡与余波
经过三次庭审和专家质证,法院在2025年3月作出一审判决。法官认为,保险公司健康告知表的提问过于笼统,未尽到明确询问义务,且刘先生的高血压未确诊,死亡原因也与该症状无直接因果关系。根据《保险法》第三十条,保险合同争议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。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全额保额100万元,但因林芳未及时核查丈夫的健康记录,需自行承担部分诉讼费用。
判决后,林芳泪流满面:“这钱是老刘用命换来的,总算能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了。”保险公司未上诉,但内部调整了健康告知表的设计,增加了具体疾病选项,以减少类似争议。
逝者未尽的遗愿
这场官司不仅是一场理赔之争,更是对人身生命保险核心价值的拷问。法律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,但保险公司在销售环节的疏忽和条款的模糊性,往往让普通家庭在失去亲人后雪上加霜。林芳的坚持,不仅为家人争取了应有的保障,也为丈夫的最后托付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。
判决后,林芳用赔偿金还清了债务,剩余的钱为孩子们设立了教育基金。她在丈夫的墓前轻声说:“老刘,你放心,孩子们我会照顾好。”这份保险的意义,早已超越了金钱,而是对爱与责任的延续。